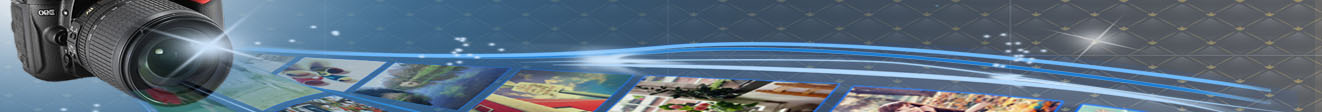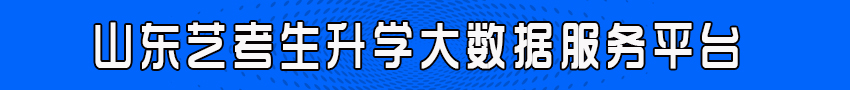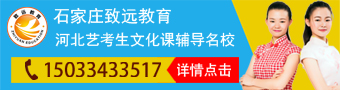“繪畫機器”式美術教育值得格外警惕
牛克誠(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
與其他高等教育不同,高等美術教育是以技藝為通道進入對于學生的整體培養系統之中的。
美術作品或造型的呈現總是與某一特定的技藝相聯系,而這種技藝又是由人的雙手來操作完成的。無論是平面的繪畫還是立體的雕塑,無不依靠一雙雙靈巧敏感的手把它們描繪、雕琢刻畫出來;藝人的想象力及創造力,憑借手的操作能力而形諸畫面或立體空間。手藝,成為人區別于其他動物、凝結著豐沛情感與智力的高級能力。
從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及原始洞窟壁畫到新石器時代的磨制石器及彩陶,人類從最開始就通過雙手來完成造型意志,隨著文明進程的不斷向前以及工具材料的不斷豐富,逐漸完善起雕塑、油畫及中國畫、書法等美術技藝。從1582年意大利畫家卡拉奇兄弟創立的波倫亞美術學院,到1648年創立的巴黎皇家繪畫雕塑學院,油畫、雕塑等美術技藝逐漸成為西方美術學院的基礎教學科目;中國畫也從1906年南京兩江師范學堂的誕生,進入到現代學院美術教育之中。時至今日,我國高等美術院校已形成國、油、版、雕、書法等基礎教學科目。可以說,這些科目緊貼人類藝術文明的發展主線,它們歷經數百年,培養并訓練著美術院校學生手的操作能力及其情智表現能力。事實證明,這樣的傳統美術科目教學,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培養出眾多美術大師。
然而,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一種追逐觀念、消解技藝、顛覆傳統美術教學的潮流,在西方似乎已蔚然成風。如今,在歐美藝術院校中已幾乎很難找到學院式的油畫或雕塑教學,美術課堂就如同工場一樣,已經不再培養學生雙手的繪、雕能力,而是鼓動他們拼命想出各種點子,然后用工業生產的形式制造出來。手的繪、雕能力,手的直接造型性以及手與造型物之間互相感應的精微的智慧能力,就在這樣的藝術教學中被消解殆盡。
油畫本是西方文明發展的產物,但它卻在五百多年后被其文明自身所拋棄。幸運的是,油畫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完成了一次世界性的傳播與擴散,通過李鐵夫、馮鋼百、李叔同、陳抱一、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龐薰琹等人傳入中國,而后成為中國高等美術教育的一個傳統科目。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油畫家把它拿來,用中國風格、中國精神、中國氣派對它進行再創造,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方針下,又通過展覽、教學等形式回到西方——那個已經把它拋棄但卻又是它的原生文化——再度綻放它的造型之美。用中國式的油畫去反哺西方,這既是文明交流的一種新生態,也將是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藝術家的必選演出。
從個人的成長能力看,隨著工業文明的到來、都市文明的興起以及科技文明的發展,人的先天能力或養成于農業文明的諸多能力,越來越被機器或高科技所代替,人類越來越趨于自身的低能或無能。當我們把電話號碼交給了通訊錄,把記事通知交給了手機拍攝,把一項項工作計劃交給了電子文檔,我們的記憶能力也就慢慢被電子設備所吞噬。同理,我們身體與手的能力不也正在日益消失嗎?《莊子》所說的承蜩、蹈水、削木之技于今天就是一個神話般的存在。如果按照當代西方藝術院校的美術教學,在人類諸多技藝的譜系中,不是要永遠失去畫畫的能力、雕塑的能力嗎?西方印象派之后不斷否定從前、不斷創新語言的藝術突進,以至把架上繪畫及傳統雕塑形態都給全盤否定,表現出西方文明的斷裂式發展特征,它一方面在文化整體上凌越其自身的文明創造,一方面也在個體成長上阻撓著人的全面發展。
因此,當代中國高等美術教育還能把油畫、雕塑等傳統美術類型作為主體科目,既表明我們對于這一人類文明成果的高度禮贊,也是為著讓未來的人們永遠葆有以手藝為根本的造型能力。特別是在以計算機為主要創作手段的圖像時代,這種具有人類情感溫度與歷史文明厚度的手藝創造,就更有意義。
當然,如果僅僅是技藝的教育,培養的還只是學生的一種片面能力,而并非全面發展。只有一技之長的“繪畫機器”美術教育需要格外警惕。因此,在高等美術教育的學生能力培養中,除了手藝,也更要注重“心質”。強調對學生的情懷、品格、學養及觀念意識的綜合培養。所謂的“心手相應”已經表明,手的能力需要在心力的驅動下呈現出來。心田的豐饒或貧瘠,決定了手藝之花的鮮活或凋敝。只有心質的豐盈飽滿,才能賦予雙手不竭的創造力,才能讓藝作的雙手,觸摸到那精神高華的圣地。
與此同時,高等院校的美術教育也還需要培養學生的另一種能力——“眼力”,它是與“手藝”“心質”同樣重要的第三種能力。這種能力不是被動的視覺接受,而是要學會通過視覺能力和審美智性訓練,提高雙眼的洞悉能力,通過認知和分析視覺對象而洞穿事物的本質,既要養成批判性的視覺識讀能力,也要養成建設性的視覺秩序建構能力,以創新性的視覺思維建構富于時代精神的知識結構體系,從而為他們未來的美術創造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