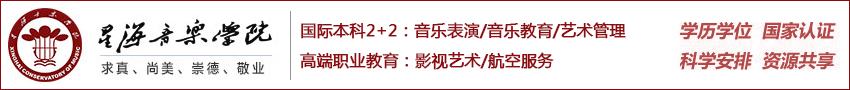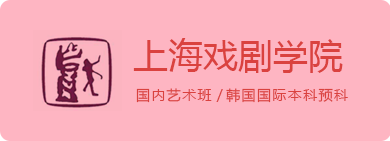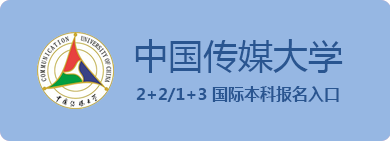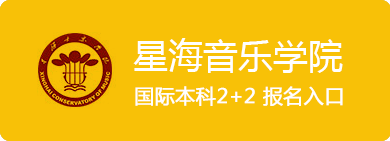音樂不應有雅俗之分
作為一個音樂教育工作者,筆者自認對音樂的基本概念還算熟稔,但前幾天有學生問我“何為高雅音樂”,我卻被問倒了。請教了相關學者,翻遍各種音樂教科書,我也沒找到任何關于“高雅音樂”的定義。
可有意思的是,“高雅音樂”的概念已在現實中被廣泛使用。比如,媒體就經常使用“高雅音樂如何親民”之類的標題,一些學者甚至還以“高雅音樂”為研究對象,撰寫了不少論文,像“影響高雅音樂走向大眾的幾個因素”“淺談高雅音樂如何進入中等城市音樂市場”。
如果音樂有高雅的,與之對應,必然得有庸俗的(或低俗的)。那我們又該以什么樣的標準來評判一種音樂是高雅還是低俗呢?
音樂的雅俗之辯大概可以追溯至《詩經》。根據受眾群體和使用范圍的不同,《詩經》中的內容分為風、雅、頌三類。風是來自民間的音樂,大部分是民歌;雅是周王室的宮廷音樂,即所謂正聲雅樂。到了隋唐,有了明確的“雅樂”“俗樂”概念,分別指代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此二者雖然在內容、曲調等方面有所差異,但最主要的區別還是使用人群不同,所以雅樂并非指高雅的音樂,俗樂也非庸俗、低俗的音樂。古代將音樂分為雅與俗,更多是為了將使用雅樂的統治者和使用俗樂的被統治者區分開來,以方便統治階級的統治。
今天,人們談論的“高雅音樂”跟古時候的雅樂不是一回事,主要指格調高、有品位的音樂。從現實中看,有人將西洋古典音樂視為“高雅音樂”,有人將現代交響樂視為“高雅音樂”,還有人將在高大上的音樂廳里演奏的音樂視為“高雅音樂”。這些音樂或主題宏大,或內容深刻,或配器復雜,或演奏難度大,但這一切跟格調高低、是否雅致有什么關系呢?
如果說古時候統治階級將一些音樂貼上“雅”的標簽是統治的需要,那現代社會一些音樂仍被賦予“高雅”的身份,除了傳統習慣的因素,恐怕還有更多利益糾葛。比如,現實中就有不少人將欣賞“高雅音樂”視為品位、身份的象征,似乎走進音樂廳聽了場古典交響樂,自己的藝術素養和文化品位一下子就提升了不少。正是把握了這種心理,很多大企業喜歡贊助古典音樂院團的創作和演出(事實上,現在國外的古典樂團基本都靠大財團的支持才得以生存),并且將演出票作為禮品贈送給客戶。不管是否去觀看演出,客戶往往都因獲贈了一張“高雅音樂”的入場券而得到了心理上的滿足,而企業通過跟“高雅音樂”綁定,也獲得了形象宣傳的機會。
作為藝術的音樂是面向所有人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以談不上高雅和不高雅之說,不同的作品之間體現的也只是風格的不同。從傳播推廣音樂藝術的角度,也不應該對音樂進行雅俗之分。冠名“高雅”二字,對于聽眾而言,往往是一種心理負擔。現實生活中提起“高雅音樂”,經常聽人說“太高雅了,理解不了,還是不去聽了”。看似褒揚的“高雅”二字,人為地將“高雅音樂”置于了高高在上的位置,意外地為“高雅音樂”的傳播推廣設置了障礙。這或許也是上述所謂“高雅音樂”受眾群體一直較小的一個原因。
還有人提出,音樂中的“雅俗”,“雅”是高雅,“俗”卻并非庸俗、低俗,而是通俗。在人類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時代,一般的人對于一些技法復雜、思想晦澀的音樂難以理解,而更適合欣賞表達直白、內容簡單的音樂。那種時代背景下,對音樂進行雅俗分類有一定的必要。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藝術素養和藝術鑒賞力也在不斷提升,比如重慶市迎龍鎮北斗村村民就成立了一支農民管樂隊,還登上了國家大劇院的舞臺。因此,所謂不同觀眾的欣賞力、理解力有很大差異,不應再成為繼續對音樂進行雅俗之分的借口。
所有的藝術都在平凡中孕育著偉大,又在偉大中孕育著平凡。古典音樂并不高深,流行音樂也并不庸俗,所有的音樂都是人類表達情感的手段,都有其美的地方,這種美需要個體用心去品味,而無需別人用標簽去標示。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