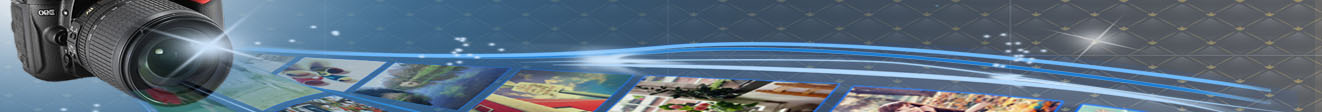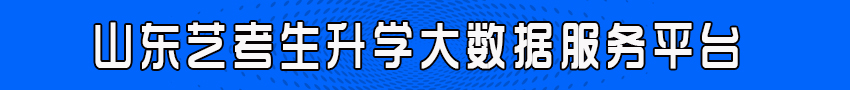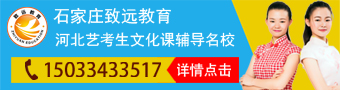關于我國音樂學學科建設的幾點想法
不久前,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幾次不同的重要場合,鄭重提出了要重視發展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并提出在這個領域力求“創新”的要求,引起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受到極大鼓舞。一個國家、民族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和發展,終究離不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這兩個翅膀,否則就很難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未來的騰飛。
音樂學作為人文學科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看來,它的任務是在理論和歷史這兩個層面上對音樂這門藝術進行多方位、多側面的思考和探究。關于這門學科對于我國音樂文化整體發展的意義,我在十年前為一部音樂學文集撰寫的一篇序言中有過這樣一段話:“一位偉大的先哲曾經高屋建瓶地講過這樣一句深刻的話:‘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發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恩格斯《反杜林論》序言)這句話或許能啟示我們:一個民族的音樂文化整體的高度發展,恐怕也是不能離開音樂理論思維的深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音樂學這門學科的建設在一個民族的音樂文化整體發展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對音樂文化的人文思考,中國古代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輝煌燦爛的成果。但當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隨著音樂文化的蓬勃發展,對音樂文化的學術研究也有了迅速的發展,終于建立了近代意義上的音樂學“學科”時,由于種種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中國在這方面卻逐漸落在了后面。直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前后,作為近代意義上的“音樂學”學科才在第一代音樂學者王光祈、蕭友梅等人的努力之下,奠定了初步的基礎,而它真正的發展則是在共和國建立之后,特別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在這半個世紀的歷程中,學科終于逐漸形成,它體現在:音樂學的研究機構和人才培養的教學基地從草創到最后建立,一支專業性的學術研究隊伍逐漸形成,大規模的民族民間音樂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陸續展開并取得豐碩成果;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近二十多年來,學科的建設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各音樂院校中的音樂學專業陸續普遍建立并逐步成熟,一大批不同年齡段的音樂學工作者活躍在科研第一線上,音樂學子學科各自得到發展,各子學科的學會紛紛建立并有力地推動了音樂學術的發展。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國音樂學的學科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先后建立了諸如中外音樂史學、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聲學和律學,以及近期已經起步的世界民族音樂、音樂聲學、音樂心理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治療學等等一系列子學科。這些子學科雖然在形成的歷史、研究力量,以及研究的深度和成果方面尚不平衡,但一個學科體系的框架畢竟已經形成。這一切都已經為中國音樂學未來的發展打下了一個良好的、比較堅實的基礎。可以說,中國音樂學,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人文學科,已經登堂入室。
然而,對于中國的音樂學家們來說,面前是一個艱辛的路程。應該承認,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人文學科,中國的音樂學還很年輕。在這個學科的一些領域,我們同當代西方音樂學的最高成就相比,是有距離的。特別是在“創新”這一點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重而道遠。考慮到我國音樂學學科的長遠建設,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需要我們關注:即擴大學科的學術視野,加強理論與歷史的相互融合和滲透,重視對音樂本體的研究。
一、擴大學科的學術視野
音樂學這門學科本身是一個多門類的音樂知識系統,如前所述,其內部已經形成一個由一系列子學科諸如音樂史學、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心理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技法理論等等構成的學科體系結構,它們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而與此同時,音樂學作為一個人文學科,它又與本學科之外的一系列諸如哲學、史學、美學、藝術學、民族學、心理學、社會學,乃至數學、音響學等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密切聯系。
發源于西方的近代音樂學,其所以能從諸多人文學科中獨立出來,并能最終形成由上述分門別類的諸多子學科構成的學科體系,這不能不歸功于西方人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在科學領域長期形成的長于縝密分析的思維方式。然而,這種思維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便顯露其自身的局限。恩格斯在充分肯定這種思維方式對推動科學發展的巨大貢獻的同時,也指出這種相對靜止、孤立的思維方式被培根和洛克移用到哲學領域來以后的消極的一面:“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遲早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要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了它們相互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了它們的產生和消失;看到它們的靜止,忘了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恩格斯的這些話,對我們當今推動和深化音樂學學科建設,很有啟示。
擴大學科的學術視野,實現學術上的互補和相互滲透,意識到學科之間的“普遍聯系”,這對我國音樂學學科的發展和深化,具有戰略性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在與音樂學相關的一系列人文學科迅速發展、音樂學子學科相繼形成的今天,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學術視野的狹窄特別表現在:音樂學與其他相關人文學科之間、音樂學各子學科之間、甚至子學科的內部相互疏離甚至隔絕的現象相當普遍。僅以我比較熟悉的音樂史學和音樂美學領域為例,音樂史學缺乏對整個當代中外史學理論的關注;在對中國的和西方的音樂歷史研究之間缺乏相互溝通,甚至在中國的或西方的音樂歷史研究中,將古代和近現代相互分割、忽視整體性研究,而相似的情況,在音樂美學領域中,在不同程度上同樣存在。這種情況,在其他子學科中恐怕也同樣值得關注和審視。這種局面,對音樂學的學科建設和深化,顯然是非常不利的。音樂學學科本身,特別是其一系列子學科本身,在性質上本來就具有很強的邊緣性和交叉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擴大自身的學術視野,忽視甚至放棄在不同學科之間的邊緣和交叉點上尋找學術的生長點,那么,在我看來,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恐怕是很難實現的。這是一件非常艱巨而復雜的工作,需要長期扎實堅韌的探索,容不得半點草率,學術上沒有任何省事的“捷徑”可走。
在擴大學科的學術視野時,有一個如何對待西方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成果問題。這一向是個敏感的問題。我認為,一是要具有一種敢于大膽吸取人類思想領域中一切優秀成果的勇氣和能容納百川的寬闊心胸。我始終認為,一般說來一種深刻、嚴肅的學術成果都不大可能是全無價值、一無是處,其中總有某些值得我們思考甚至借鑒的東西。二是要在認真研讀、真正弄清各種學說實質的前提下,保持一種冷靜的分析、鑒別的態度,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在這方面我們應該作一些扎扎實實的工作,不久前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組織翻譯力量與一家出版社簽訂了翻譯出版十部西方音樂學界有定評的學術專著,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重溫魯迅先生雜文《拿來主義》中的一席話,至今仍是不無教益的:“……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二、加強理論與歷史的相互融合和滲透
如前所述,音樂學,作為一種人文學科,本來就是一門既從理論的、又從歷史的層面對音樂文化整體進行多方位、多側面研究的學科。這門學科的性質本身就要求我們不宜將理論和歷史這兩個層面機械地隔絕開來,理想的做法應該是將二者有機地融合起來,相互滲透,使我們的音樂學研究既有充分的理論深度,又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在我看來,這應該是音樂學這門學科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
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那段話,更使我們意識到在音樂學研究中理論中思維的重要性,理論思維的貧乏恐怕是很難使我們登上這門學科的高峰的。以子學科音樂史學研究為例,它的任務當然是要發現、梳理、研究音樂發展的各種具體史實、事件,并在此基礎上作清晰的整體描述,形成一個具體、完整的音樂歷史景觀。然而,這還不是音樂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境界。音樂歷史同整個人類歷史一樣,其發展有它自己的內在規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為使研究能從令人眼花繚亂的、曲折的種種事實和偶然現象中脫身,進入探索規律的層次,就只能依靠理論的、邏輯的思維。其實,民族音樂學研究也好,世界音樂研究也好,何嘗不是如此?現象、事實的收集和羅列,難道就是這些學科的更高要求和最終目的嗎?一位音樂史學家,如果完全同相關的哲學、史學理論、藝術學、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心理學等理論層面疏離,甚至不屑一顧,那么,要使中國的音樂史學(不論是中史,還是外史)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重大的突破,恐怕是相當困難的。
音樂學既然是一種人文學科,它就不能不關注歷史,強化自身的歷史意識。馬克思主義極端重視歷史,認為歷史有兩種,即自然界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歷史,并且認為 “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并宣稱:“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關于歷史與相關人文科學領域的關系,他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必須重新研究全部。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