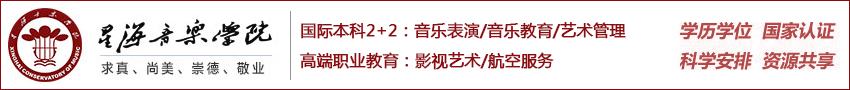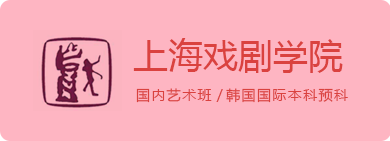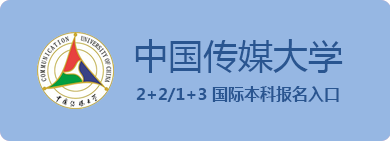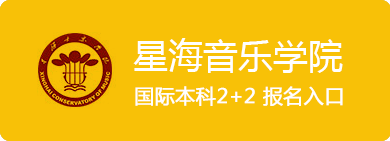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
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有關(guān)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在20世紀(jì)歷史的論述,都戛然而止于1966年。重新再續(xù),則從1980年后開始。于是,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在20世紀(jì)的歷史,就分成了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兩段。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就是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的一片空白?是因為這段歷史屬于討論的禁區(qū)?還是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民族音樂學(xué)的中國之路,真的在文革中斷了?
筆者認(rèn)為,“禁區(qū)”的立論不成立。其一,海外的學(xué)者并不存在意識形態(tài)的禁忌問題;況且,即便在中國大陸,音樂界對“文革”或“文革音樂”的反思和研究,亦始自文革的結(jié)束。雖然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末,這種反思和研究多半是以對文革中“四人幫”所推行的“陰謀文藝”,使“中國音樂事業(yè)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災(zāi)難和大破壞”的批判為主,而更傾向于反思;到1990年代至今,這種反思和研究逐漸褪去了“大批判”的氣勢,并深入到對文革中各音樂事象的研究層面了。其中包括了對文革歌曲的研究(毛主席語錄歌曲、造反歌曲、派性歌曲、紅衛(wèi)兵歌曲、知青歌曲、戰(zhàn)地新歌等)、對樣板戲的研究、對器樂曲創(chuàng)作改編的研究等等。但在這些研究中,即便如《中國“文革”音樂史》的系列研究[2],也沒有相關(guān)于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或者說是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在文革中的話題。
那么,人們是否真的相信文革中這個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是空白的?如果真的是空白,這個空白的標(biāo)記是什么?學(xué)術(shù)刊物的停止?研究機(jī)構(gòu)的解散?高等音樂院校的停課?學(xué)者的勞動改造?還是如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學(xué)家梁茂春對“文革中音樂理論”的定位,即“嚴(yán)格來講‘文化大革命’期間并沒有真正的音樂理論。它只有音樂方面的‘大批判’和‘大吹捧’。‘文化大革命’中,‘音樂理論’自始至終貫穿著對中、外優(yōu)秀作品和優(yōu)秀音樂家的蠻不講理的‘批判’與全盤否定,也貫穿著對‘樣板戲’和江青文藝路線的肉麻無恥的吹捧。這鮮明地體現(xiàn)出為‘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線服務(wù)的特點(diǎn)。”(1966:20)而本文所涉及的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亦即當(dāng)時的“民族音樂理論研究”應(yīng)該也概括在這一“音樂理論”的范圍中。
筆者認(rèn)為,上述所謂“空白”的標(biāo)記僅僅是一個表面的現(xiàn)象。文化大革命并非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空場。對此,本文將從下述幾個方面開展討論。
一、群體與個體
此處的群體,包括兩層意思。第一是實(shí)體性的,即民族音樂學(xué)者的群體,以及這個群體在那個特殊年代普遍遭遇的命運(yùn);第二是觀念性的,即那個特殊的時期給人們留下的社會歷史印象,也就是社會群體的歷史記憶,比如“十年浩劫”。
就群體而言,文革對于學(xué)術(shù)的災(zāi)難性破壞,已經(jīng)被認(rèn)同。問題是,在群體的命運(yùn)及其歷史記憶之外,對個體生命(即民族音樂學(xué)者個人)在這個特殊時期的經(jīng)歷的考察,是否有助于我們更細(xì)致地去分析這段歷史呢?
筆者不止一次地聽導(dǎo)師喬建中提起他在京劇院期間為曾有“四小名旦”之稱的張君秋記錄傳統(tǒng)唱腔,從中收獲了戲曲音樂的滋養(yǎng)。聽王耀華說他在步行串連途中,對福建閩西、江西井岡山地區(qū)、湖南韶山、瀏陽、岳陽,以及武漢,廣西柳州等地革命民歌的學(xué)習(xí)和采錄。在采錄的過程中,他又如何逐步掌握了四句頭、五句頭山歌的特征。聽沈洽說他在贛州下放時考察興國山歌,并對其中方言調(diào)值進(jìn)行歸類,并考察其與音高的關(guān)系,通過記譜,發(fā)現(xiàn)了當(dāng)時興國山歌研究的一些問題。比如興國山歌有一些音的音高是介于do跟tsi之間,容易形成同主音轉(zhuǎn)換的調(diào)式變化等等。[3]作為學(xué)生,我在聽到這些口述的個人經(jīng)歷時,第一個反應(yīng)即是:文化大革命如果真是學(xué)術(shù)的空場,那么我的這些師長,在1980年后,又怎么會突然地成熟為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領(lǐng)域的一代人物?他們的成熟與后來的發(fā)展,與這個特殊年代的際遇是否能夠分離?
同樣,包括老一輩的人物,如楊蔭瀏在干校期間,勞動之余繼續(xù)潛心于中國音樂史的著述,它與1981年《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下)正式出版豈能無關(guān)?黃翔鵬在負(fù)責(zé)管理干校菜圃的艱苦勞動下,致力于中國古代音樂理論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4],這和他文革之后轉(zhuǎn)向中國古代音樂史以及傳統(tǒng)樂學(xué)理論的研究不無關(guān)系。
還有如筆者的同齡人,紅衛(wèi)兵樂團(tuán)有關(guān)《毛主席詩詞大聯(lián)唱》、《秋收起義》《井岡山的道路》的演出,“八個樣板戲”從頭到尾迭唱不休的經(jīng)歷,那些《戰(zhàn)地新歌》和《外國民歌200首》交織成的青春……幾乎成為我們重要的音樂積累。其中的民族旋律、民族音調(diào)伴隨著后來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歲月,在我們的學(xué)術(shù)生涯中又種下了什么樣的種子?
如此等等,都提示我們對“文革”中各類音樂活動的研究,除了被公認(rèn)為“十年浩劫”的歷史定位之外,除了群體在特定的社會時期形成的表象之外,我們還應(yīng)該關(guān)注個體的生存與歷史的關(guān)系。通過對民族音樂學(xué)者個人經(jīng)歷的挖掘,或通過自傳的、個體歷史的敘述,描繪歷史的多元景觀,以發(fā)現(xiàn)“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diǎn)”(DonaldA.Ritchie,1995:29),發(fā)現(xiàn)在這些個體的經(jīng)歷中,可能存在著影響歷史的因素。
當(dāng)然,在考察個體和群體記憶的關(guān)系中,我們也不能忽視,在某種情況下,個體的記憶往往會被集體的記憶所遮蔽。比如,筆者在采訪某位師長時,從不經(jīng)意的言談中得知該師曾于文革中對當(dāng)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進(jìn)行過訪談,并在其后撰寫了有關(guān)革命樣板戲創(chuàng)作中如何將民族舞蹈語匯和芭蕾舞相結(jié)合的長文。然而,這篇發(fā)表于當(dāng)年《解放軍報》上的重要文章,卻幾乎被當(dāng)事人自己遺忘了。[5]這種遺忘,不是孤例。除了當(dāng)事人潛意識中的價值判斷之外,形成這種判斷的,因社會群體對于那個時代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亦無疑是使這種記憶抹消,甚至可說是集體記憶對個人記憶強(qiáng)制抹消的重要因素。這正說明個體的、自傳式的調(diào)查研究所需要的細(xì)致與深入。
因此,筆者不太贊同這樣的一種籠統(tǒng)判斷,即或者認(rèn)為“文革”中沒有真正的音樂理論,或者將許多音樂工作者或民族音樂學(xué)者在文革夾縫中堅持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簡單地視為一種與“錯誤的政治路線和文藝路線進(jìn)行了正氣凜然的抵制”。尤其是將那個時代留下的被認(rèn)為是較好的作品,僅僅視為一種斗爭的結(jié)果。抵制和斗爭,是一個層面,但不是全部的層面。其中還有個人品格和藝術(shù)追求的相契,有學(xué)術(shù)路向在特殊際遇中的承接和探索,甚至還有命運(yùn)和興趣的左右。這一點(diǎn),我將于后續(xù)的論述中進(jìn)一步展開。
二、歷時的起伏
所謂歷時的起伏,指的是“文革十年”并非鐵板一塊的均質(zhì)的“浩劫”。從1966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jì)要》的發(fā)表,提出存在著一條“資產(chǎn)階級的文藝思想,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jié)合”的黑線,并要“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后,再到1975年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兩次談話以及對電影《創(chuàng)業(yè)》的批示,鄧小平復(fù)出主持國務(wù)院工作,再到“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文革在政治的權(quán)力斗爭中,可以區(qū)分為不同的歷史階段,并呈現(xiàn)出民族音樂學(xué)發(fā)展的起伏。
從刊物上看,原有的學(xué)術(shù)刊物如《音樂研究》等紛紛遭遇停刊,連《人民音樂》這類黨在音樂界的喉舌,也于1966年第二期后銷聲匿跡。當(dāng)時,間或出版的音樂期刊多是歌曲一類,如《紅小兵歌曲》、《解放軍歌曲》《群眾歌曲》等。翻閱這些歌曲期刊,只能在零星的“創(chuàng)作談”一類文字中找到和民族音樂學(xué)相關(guān)的蛛絲馬跡。
原有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確實(shí)凋敝了。如現(xiàn)在的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從文革開始,正常的研究項目和資料搜集、整理工作都被迫停止。1969年3月,全所人員除3人留守外,其余皆下干校勞動、學(xué)習(xí)。直至1972年,該所人員才分批陸續(xù)回京,為恢復(fù)研究所的工作做準(zhǔn)備。1973年4月,該所回北京的部分研究、資料人員組成了由文化部藝術(shù)研究機(jī)構(gòu)領(lǐng)導(dǎo)的音樂舞蹈室音樂組,同年8月,受命成立了《中國音樂史》《西洋音樂史》兩個編寫組,征調(diào)全國各地音樂院校人員參與編寫,1975年11月和1977年,分別完成了《中國古代音樂簡史》和《歐洲音樂史》。同時,中國音樂史編寫組同時編輯整理出一套中國音樂史樂譜和音響資料。[6]當(dāng)然,編史的工作雖然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被要求要突出儒法斗爭的觀點(diǎn),但參與人員,依然在夾縫中開展了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認(rèn)真研究。比如,借調(diào)到北京參與中國古代音樂史修編的上海音樂學(xué)院的夏野,在工作中“得有機(jī)會與許多專家和同行們詳細(xì)討論有關(guān)中國音樂史的教學(xué)、研究工作”,獲得了不少教益,并將這些教益吸收進(jìn)了他完成于1983年,出版于1989年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7]這部史書,至今仍是上海音樂學(xué)院中國古代音樂史的教材。
從高等音樂院校來看,教學(xué)的停滯與恢復(fù)時間與上述研究機(jī)構(gòu)相似。1972年,上海音樂學(xué)院開辦“五·七音訓(xùn)班”,招收6年制面向工農(nóng)兵子弟的專科學(xué)生。1973年“中央五·七藝術(shù)大學(xué)”成立,音樂系科由原來的中央音樂學(xué)院和中國音樂學(xué)院合并。在民族音樂理論的教學(xué)中,秉承舊制,按體裁分類,開設(shè)了民族器樂、戲曲、民歌等課程。其中除了戲曲教學(xué)只能分析京劇“樣板戲”及其移植劇目外,其它體裁類別的教學(xué),還是由教師自行編撰教材[8]。期間,民歌教研組的耿生廉等教師,曾經(jīng)國務(wù)院文化組的批準(zhǔn),到南方各地采集民歌。其選編的民歌教材的主體內(nèi)容,一直沿用至1990年代初。民族器樂教師周宗漢,于“四人幫”垮臺前夕,遠(yuǎn)赴新疆帕米爾高原,搜集和整理塔吉克族的民間器樂,并于文革結(jié)束后撰文發(fā)表了《塔吉克族的樂器》連載文章。
如此等等,透露出那個時代政治斗爭的曲折與專業(yè)建設(shè)的起伏。最明顯的,是以1972年左右作為文革十年歷史分期的一個界點(diǎn),即在1971年秋天林彪死亡,1973年春天鄧小平復(fù)出工作,呈示出“文革十年”的前五年與后五年的不同局面。此外,可以設(shè)問的是,當(dāng)民族音樂學(xué)領(lǐng)域得到了喘息的機(jī)會,人們是怎么開始建設(shè)的?比如,通過上述民族音樂理論學(xué)科教學(xué)的點(diǎn)滴事件進(jìn)一.........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就是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的一片空白?是因為這段歷史屬于討論的禁區(qū)?還是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民族音樂學(xué)的中國之路,真的在文革中斷了?
筆者認(rèn)為,“禁區(qū)”的立論不成立。其一,海外的學(xué)者并不存在意識形態(tài)的禁忌問題;況且,即便在中國大陸,音樂界對“文革”或“文革音樂”的反思和研究,亦始自文革的結(jié)束。雖然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末,這種反思和研究多半是以對文革中“四人幫”所推行的“陰謀文藝”,使“中國音樂事業(yè)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大災(zāi)難和大破壞”的批判為主,而更傾向于反思;到1990年代至今,這種反思和研究逐漸褪去了“大批判”的氣勢,并深入到對文革中各音樂事象的研究層面了。其中包括了對文革歌曲的研究(毛主席語錄歌曲、造反歌曲、派性歌曲、紅衛(wèi)兵歌曲、知青歌曲、戰(zhàn)地新歌等)、對樣板戲的研究、對器樂曲創(chuàng)作改編的研究等等。但在這些研究中,即便如《中國“文革”音樂史》的系列研究[2],也沒有相關(guān)于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或者說是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在文革中的話題。
那么,人們是否真的相信文革中這個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是空白的?如果真的是空白,這個空白的標(biāo)記是什么?學(xué)術(shù)刊物的停止?研究機(jī)構(gòu)的解散?高等音樂院校的停課?學(xué)者的勞動改造?還是如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學(xué)家梁茂春對“文革中音樂理論”的定位,即“嚴(yán)格來講‘文化大革命’期間并沒有真正的音樂理論。它只有音樂方面的‘大批判’和‘大吹捧’。‘文化大革命’中,‘音樂理論’自始至終貫穿著對中、外優(yōu)秀作品和優(yōu)秀音樂家的蠻不講理的‘批判’與全盤否定,也貫穿著對‘樣板戲’和江青文藝路線的肉麻無恥的吹捧。這鮮明地體現(xiàn)出為‘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線服務(wù)的特點(diǎn)。”(1966:20)而本文所涉及的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亦即當(dāng)時的“民族音樂理論研究”應(yīng)該也概括在這一“音樂理論”的范圍中。
筆者認(rèn)為,上述所謂“空白”的標(biāo)記僅僅是一個表面的現(xiàn)象。文化大革命并非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空場。對此,本文將從下述幾個方面開展討論。
一、群體與個體
此處的群體,包括兩層意思。第一是實(shí)體性的,即民族音樂學(xué)者的群體,以及這個群體在那個特殊年代普遍遭遇的命運(yùn);第二是觀念性的,即那個特殊的時期給人們留下的社會歷史印象,也就是社會群體的歷史記憶,比如“十年浩劫”。
就群體而言,文革對于學(xué)術(shù)的災(zāi)難性破壞,已經(jīng)被認(rèn)同。問題是,在群體的命運(yùn)及其歷史記憶之外,對個體生命(即民族音樂學(xué)者個人)在這個特殊時期的經(jīng)歷的考察,是否有助于我們更細(xì)致地去分析這段歷史呢?
筆者不止一次地聽導(dǎo)師喬建中提起他在京劇院期間為曾有“四小名旦”之稱的張君秋記錄傳統(tǒng)唱腔,從中收獲了戲曲音樂的滋養(yǎng)。聽王耀華說他在步行串連途中,對福建閩西、江西井岡山地區(qū)、湖南韶山、瀏陽、岳陽,以及武漢,廣西柳州等地革命民歌的學(xué)習(xí)和采錄。在采錄的過程中,他又如何逐步掌握了四句頭、五句頭山歌的特征。聽沈洽說他在贛州下放時考察興國山歌,并對其中方言調(diào)值進(jìn)行歸類,并考察其與音高的關(guān)系,通過記譜,發(fā)現(xiàn)了當(dāng)時興國山歌研究的一些問題。比如興國山歌有一些音的音高是介于do跟tsi之間,容易形成同主音轉(zhuǎn)換的調(diào)式變化等等。[3]作為學(xué)生,我在聽到這些口述的個人經(jīng)歷時,第一個反應(yīng)即是:文化大革命如果真是學(xué)術(shù)的空場,那么我的這些師長,在1980年后,又怎么會突然地成熟為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領(lǐng)域的一代人物?他們的成熟與后來的發(fā)展,與這個特殊年代的際遇是否能夠分離?
同樣,包括老一輩的人物,如楊蔭瀏在干校期間,勞動之余繼續(xù)潛心于中國音樂史的著述,它與1981年《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下)正式出版豈能無關(guān)?黃翔鵬在負(fù)責(zé)管理干校菜圃的艱苦勞動下,致力于中國古代音樂理論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4],這和他文革之后轉(zhuǎn)向中國古代音樂史以及傳統(tǒng)樂學(xué)理論的研究不無關(guān)系。
還有如筆者的同齡人,紅衛(wèi)兵樂團(tuán)有關(guān)《毛主席詩詞大聯(lián)唱》、《秋收起義》《井岡山的道路》的演出,“八個樣板戲”從頭到尾迭唱不休的經(jīng)歷,那些《戰(zhàn)地新歌》和《外國民歌200首》交織成的青春……幾乎成為我們重要的音樂積累。其中的民族旋律、民族音調(diào)伴隨著后來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歲月,在我們的學(xué)術(shù)生涯中又種下了什么樣的種子?
如此等等,都提示我們對“文革”中各類音樂活動的研究,除了被公認(rèn)為“十年浩劫”的歷史定位之外,除了群體在特定的社會時期形成的表象之外,我們還應(yīng)該關(guān)注個體的生存與歷史的關(guān)系。通過對民族音樂學(xué)者個人經(jīng)歷的挖掘,或通過自傳的、個體歷史的敘述,描繪歷史的多元景觀,以發(fā)現(xiàn)“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diǎn)”(DonaldA.Ritchie,1995:29),發(fā)現(xiàn)在這些個體的經(jīng)歷中,可能存在著影響歷史的因素。
當(dāng)然,在考察個體和群體記憶的關(guān)系中,我們也不能忽視,在某種情況下,個體的記憶往往會被集體的記憶所遮蔽。比如,筆者在采訪某位師長時,從不經(jīng)意的言談中得知該師曾于文革中對當(dāng)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進(jìn)行過訪談,并在其后撰寫了有關(guān)革命樣板戲創(chuàng)作中如何將民族舞蹈語匯和芭蕾舞相結(jié)合的長文。然而,這篇發(fā)表于當(dāng)年《解放軍報》上的重要文章,卻幾乎被當(dāng)事人自己遺忘了。[5]這種遺忘,不是孤例。除了當(dāng)事人潛意識中的價值判斷之外,形成這種判斷的,因社會群體對于那個時代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亦無疑是使這種記憶抹消,甚至可說是集體記憶對個人記憶強(qiáng)制抹消的重要因素。這正說明個體的、自傳式的調(diào)查研究所需要的細(xì)致與深入。
因此,筆者不太贊同這樣的一種籠統(tǒng)判斷,即或者認(rèn)為“文革”中沒有真正的音樂理論,或者將許多音樂工作者或民族音樂學(xué)者在文革夾縫中堅持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簡單地視為一種與“錯誤的政治路線和文藝路線進(jìn)行了正氣凜然的抵制”。尤其是將那個時代留下的被認(rèn)為是較好的作品,僅僅視為一種斗爭的結(jié)果。抵制和斗爭,是一個層面,但不是全部的層面。其中還有個人品格和藝術(shù)追求的相契,有學(xué)術(shù)路向在特殊際遇中的承接和探索,甚至還有命運(yùn)和興趣的左右。這一點(diǎn),我將于后續(xù)的論述中進(jìn)一步展開。
二、歷時的起伏
所謂歷時的起伏,指的是“文革十年”并非鐵板一塊的均質(zhì)的“浩劫”。從1966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jì)要》的發(fā)表,提出存在著一條“資產(chǎn)階級的文藝思想,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jié)合”的黑線,并要“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到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后,再到1975年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兩次談話以及對電影《創(chuàng)業(yè)》的批示,鄧小平復(fù)出主持國務(wù)院工作,再到“反擊右傾翻案風(fēng)”,文革在政治的權(quán)力斗爭中,可以區(qū)分為不同的歷史階段,并呈現(xiàn)出民族音樂學(xué)發(fā)展的起伏。
從刊物上看,原有的學(xué)術(shù)刊物如《音樂研究》等紛紛遭遇停刊,連《人民音樂》這類黨在音樂界的喉舌,也于1966年第二期后銷聲匿跡。當(dāng)時,間或出版的音樂期刊多是歌曲一類,如《紅小兵歌曲》、《解放軍歌曲》《群眾歌曲》等。翻閱這些歌曲期刊,只能在零星的“創(chuàng)作談”一類文字中找到和民族音樂學(xué)相關(guān)的蛛絲馬跡。
原有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確實(shí)凋敝了。如現(xiàn)在的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從文革開始,正常的研究項目和資料搜集、整理工作都被迫停止。1969年3月,全所人員除3人留守外,其余皆下干校勞動、學(xué)習(xí)。直至1972年,該所人員才分批陸續(xù)回京,為恢復(fù)研究所的工作做準(zhǔn)備。1973年4月,該所回北京的部分研究、資料人員組成了由文化部藝術(shù)研究機(jī)構(gòu)領(lǐng)導(dǎo)的音樂舞蹈室音樂組,同年8月,受命成立了《中國音樂史》《西洋音樂史》兩個編寫組,征調(diào)全國各地音樂院校人員參與編寫,1975年11月和1977年,分別完成了《中國古代音樂簡史》和《歐洲音樂史》。同時,中國音樂史編寫組同時編輯整理出一套中國音樂史樂譜和音響資料。[6]當(dāng)然,編史的工作雖然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被要求要突出儒法斗爭的觀點(diǎn),但參與人員,依然在夾縫中開展了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認(rèn)真研究。比如,借調(diào)到北京參與中國古代音樂史修編的上海音樂學(xué)院的夏野,在工作中“得有機(jī)會與許多專家和同行們詳細(xì)討論有關(guān)中國音樂史的教學(xué)、研究工作”,獲得了不少教益,并將這些教益吸收進(jìn)了他完成于1983年,出版于1989年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7]這部史書,至今仍是上海音樂學(xué)院中國古代音樂史的教材。
從高等音樂院校來看,教學(xué)的停滯與恢復(fù)時間與上述研究機(jī)構(gòu)相似。1972年,上海音樂學(xué)院開辦“五·七音訓(xùn)班”,招收6年制面向工農(nóng)兵子弟的專科學(xué)生。1973年“中央五·七藝術(shù)大學(xué)”成立,音樂系科由原來的中央音樂學(xué)院和中國音樂學(xué)院合并。在民族音樂理論的教學(xué)中,秉承舊制,按體裁分類,開設(shè)了民族器樂、戲曲、民歌等課程。其中除了戲曲教學(xué)只能分析京劇“樣板戲”及其移植劇目外,其它體裁類別的教學(xué),還是由教師自行編撰教材[8]。期間,民歌教研組的耿生廉等教師,曾經(jīng)國務(wù)院文化組的批準(zhǔn),到南方各地采集民歌。其選編的民歌教材的主體內(nèi)容,一直沿用至1990年代初。民族器樂教師周宗漢,于“四人幫”垮臺前夕,遠(yuǎn)赴新疆帕米爾高原,搜集和整理塔吉克族的民間器樂,并于文革結(jié)束后撰文發(fā)表了《塔吉克族的樂器》連載文章。
如此等等,透露出那個時代政治斗爭的曲折與專業(yè)建設(shè)的起伏。最明顯的,是以1972年左右作為文革十年歷史分期的一個界點(diǎn),即在1971年秋天林彪死亡,1973年春天鄧小平復(fù)出工作,呈示出“文革十年”的前五年與后五年的不同局面。此外,可以設(shè)問的是,當(dāng)民族音樂學(xué)領(lǐng)域得到了喘息的機(jī)會,人們是怎么開始建設(shè)的?比如,通過上述民族音樂理論學(xué)科教學(xué)的點(diǎn)滴事件進(jìn)一.........

 掃碼關(guān)注,實(shí)時發(fā)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掃碼關(guān)注,實(shí)時發(fā)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相關(guān)推薦:
- [音樂學(xué)]寧德師范學(xué)院2021年福建省音樂學(xué)專業(yè)錄取分?jǐn)?shù)線
- [音樂學(xué)]江南大學(xué)2021年藝術(shù)類本科專業(yè)錄取分?jǐn)?shù)線
- [音樂學(xué)]玉林師范學(xué)院2021年藝術(shù)類本科專業(yè)錄取分?jǐn)?shù)線
- [音樂學(xué)]渤海大學(xué)2021年藝術(shù)類本科專業(yè)錄取分?jǐn)?shù)線
- [音樂學(xué)]江西中醫(yī)藥大學(xué)2021年音樂學(xué)(音樂治療方向)錄取分?jǐn)?shù)
- [音樂學(xué)]浙江師范大學(xué)2021年藝術(shù)類本科專業(yè)錄取分?jǐn)?shù)線
- [音樂學(xué)]咸陽師范學(xué)院2021年藝術(shù)類本科專業(yè)錄取分?jǐn)?shù)線
- [音樂學(xué)]寧夏大學(xué)新華學(xué)院2021年寧夏藝術(shù)類專業(yè)錄取分?jǐn)?shù)線
音樂專業(yè)課
最新資訊
熱門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