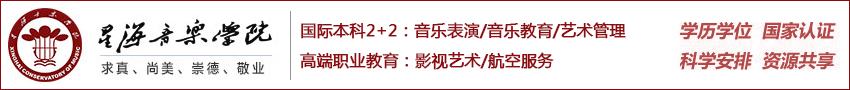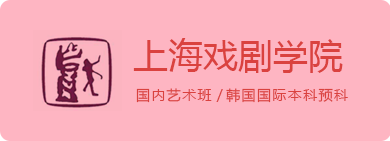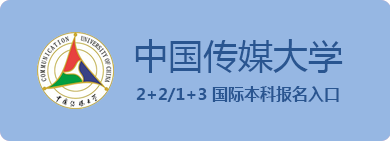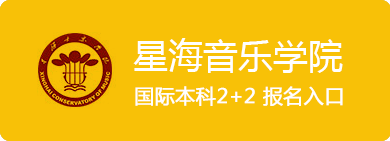攝影大師的風光攝影技巧分享
戴維·沃德——打破風光成規
打破預期
旅行攝影師得用照片向人們講述他鄉文化和異國民族。不過,我還是常常背著相機漂洋過海,我的大部分作品確實是在國外完成的。之所以要出國拍攝,是因為我總要花上一兩天時間才能進入拍攝所需的“攝入”心態,如果我待在家里忙于瑣事,就不會有意花時間調整心態。
這是挪威為數不多的“觀景點”之一。甚至有條斜坡通向岸邊,岸邊的巖石形成一個個水坑,彎曲的線條猶如刀刻; 遠方一座美麗的半島作為背景,島上群山聳立,如夢似幻。8月初的一天,我在凌晨1點攝下了這張照片。由于地處北極圈內北冰洋沿岸,這里的天空要么云團密布,要么萬里無云。幸運的話,還能捕捉到一片云層的邊緣線。當時,我加用了一塊標號為5.5的中灰漸變濾光鏡——測光表仍然顯示天空曝光過度,然而鑒于富士Velvia膠片對于黃色不如測光表所顯示的那么敏感,我知道它將凸顯某些細部特征。
驚異感
對于旅行我樂此不疲,因為需要不斷感受新的視覺體驗帶來的沖擊。換句話說,我需要驚異感,而旅行正是收獲驚異感的重要途徑。在熟悉的環境下,難免受制于預期的模式,囿于熟悉而省心的思維和活動方式。當然,這并不是說我總是跑到陌生的地方拍攝,我也會故地重游。雖然這看上去與我剛剛提出的觀點有沖突,但我確實常常在故地重游時拍出更富趣味的照片。
我本想用5×4英寸的大畫幅相機拍攝。然而當時的光線稍縱即逝,我感覺倒影很快便會消失,因此不得不用袖珍數碼相機。我喜歡這里模糊的空間感和奇異的倒影——這一切都歸功于霧氣蒸騰的溫泉水。
拍攝中的自我批判
無論在哪里拍攝,一切風光攝影都是解決構圖問題的過程。在我看來,不斷挑剔自己的作品是避免自滿和落入俗套的最佳方法!在我每年拍攝的350張照片中,真正滿意的大約只有25張。兩三年后,我可能只對其中的5張感到滿意—甚至更少。
堅持開放的思維
我出行時很少事先計劃要拍攝的影像。何苦花費大量時間作攝影計劃,計算某地的光照條件何時最為理想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寧愿隨時隨地面對各種可能。長時間的計劃研究只會讓我拍攝出意料之中的照片,因此我更傾向于在抵達目的地之后再行探索,直到發現激起我興致的景色或景物。
我樂于拍攝無名之地,因為在那里我是自由的,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表現眼前的景色。如果某景點被人們反復拍攝,再傳遞出新的信息就很難了。在我看來,攝影最重要的一點是喚起觀眾的情感。只要影像能夠激發觀眾做出反應,在哪里拍攝并不重要。
破除光線與環境的限制
旅行攝影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尋求構圖與光線的和諧平衡。在我看來,被攝景物的選取依賴于周邊環境,無論光照條件如何,我只選擇適合這一條件的景色。比起千辛萬苦地尋得一處美景后再等待合適的光線,我更傾向于根據光照條件挑選被攝體。因此,我最后拍攝的景物可能只有三英尺寬,而并非一幅遼闊的遠景圖。但是,如果當時的主要條件適合拍攝遠景圖,則必須充分把握機會。
旅行攝影的另一個要點是:打開思路,盡量把別人拍攝的照片甩到腦后,以全新的手法處理每一景每一物。假如夏天來到北極圈以北,就意味著我變成了“夜行者”,因為最佳光線出現在夜晚10點至凌晨3點之間。假如身處納米比亞的沙漠,也許意味著我將四處尋找陰影,原因是比起直射光,在反射光條件下進行拍攝更為有趣,而且更加簡單。無論我采用何種技術手段,關鍵的一點是:用孩童的眼光觀察世界,盡情欣賞大自然創造的奇跡,并用盡可能新奇的手法將它們捕捉下來。
這間破屋本是一個采礦工程師的住宅。屋頂已經損毀,只留下一根根木條。陽光透過木條照射進來,形成神秘而詭異的條紋。照片中一道門鑲嵌在另一道門中,很有點馬格利特(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的風格。
我認為這場森林大火就發生在一兩個月以前,因為灰燼仍很新鮮。由于眼前的景色是黑上加黑,拍攝這張照片是個挑戰,然而在燒焦樹皮的剝落處,仍然有些橙色的斑點,甚至有人說這看上去好像火焰未滅。
手持相機拍攝,快門速度為1.5秒,照片各部分因此不甚清晰,而我的目的正在于此。結果,這張照片玩起了光與色彩的游戲,由各種綠色擔當主角。
沃爾維丹方圓665平方英里(1,722平方公里),是非洲最大的私營自然保護區。照片中的這種草是沃爾維丹的一大特色,被稱為高大的布須曼草。正午的陽光極其刺眼,加上一陣大風吹過,即使1/2秒的快門速度也讓畫面產生了強烈的動態效果。保持草地形態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晰是很重要的,假如延長快門速度,清晰的形態便會喪失。
1960年以前,一條冰川沿著冰島南岸的這片峽谷一路向大海延伸。它消失時,留下一片潟湖和數座巨大的冰山。這些冰山漂入海中,條件具備時又被沖回岸邊。它們的顏色如同照片中那樣湛藍晶瑩。多云的天氣和天空的色調為拍攝提供了完美的環境。第二天我才發現,天氣晴朗時的拍攝效果反而欠佳。為這張照片構圖就像在拼三維拼圖,我需要不斷調整相機的位置,使三座冰山“嵌套”在一起。前面和中間的冰山大小相近,相機的位置最好起到冰山漸行漸小的效果。通過稍稍向后傾斜這架5英寸×4英寸的大畫幅相機,視角得到了改變,離我最近的冰山在視覺上被放大了,客觀上增強了“嵌套”的效果。地平線處于適當的位置也很重要。另外,我有意將冰山的倒影也包括進來,但如果位置太低,海面就顯得不夠。簡潔永遠是我的座右銘,這張照片恰恰完美體現了這一點。我希望盡量清晰而直接地呈現這幾座讓人驚嘆不已的冰山。
尼爾·本維埃用黑白思考風光
尼爾·本維埃是一位專長于自然和風光攝影的全球著名攝影家,號稱英國八位頂尖攝影大師,是國際自然保護攝影師聯盟的創始成員,出版有《創意風光攝影》和《自然攝影藝術》等暢銷攝影技法書。他對大自然有著非同一般的熱情,其創作專注于討論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其作品和訪談選入了《世界頂級攝影大師巔峰作品誕生記:風光》一書。
我承認我從來沒在暗房里好好地工作過一天。就像很多人一樣,我對于黑白攝影的接觸從來沒有到要將很多危險的化學品攪拌混和的那種地步。數碼攝影將這一切都改變了。我們可以輕松地將RAW 格式的文件轉換成為黑白照片,而且只需內有三種不同黑色墨水的臺式打印機就可以打印出質量上佳的圖片。這激勵了越來越多的彩色攝影中堅分子涉足黑白攝影。你常常可以拍出不錯的影像,但如果想要堅持下去,你需要再思考一下為什么你要追求這種轉變。
這幅影像有點憂郁,道路向明亮的天空延伸,給了人希望,讓人不禁思索從那高處可以看到什么——有可能是另一片荒涼的曠野。
尼康D3 相機,24-70mm 鏡頭,ISO 800,f/11、1/400 秒
一開始就決定
從理想化的角度來考慮,不論我們是拍彩色的還是黑白的照片,都是——或者說應該是——由敘述或表現意圖來決定的。從某些方面來講,拍彩色照片是敘述性影像的自然的選擇,因為色彩可以給攝影師的描述語言添加一些東西。但是正如我們所知,失敗的文學作品,如果故事不夠生動,即使語言再華麗也不會給作品增色多少。所以,你要自問一下:照片中的色彩是否讓你所講述的故事更完整而非只是給畫面帶來干擾?色彩的運用是否讓你對這一地方或場景的感覺更為清晰?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像許許多多的攝影記者所做的那樣,拍攝黑白照片吧。不過不要養成這樣的習慣,把色彩看作是分散注意力的元素而摒棄之,其實這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視覺疏忽。轉向黑白的原因絕不僅僅是這一點。
景色的另一面
一個場景被呈現為黑白的一個最令人信服的原因,就是營造出一種“他性”——即與我們一般的認知拉開了一段距離;它變得不那么熟悉了。這會給你的畫面帶來更強的情緒強度。充斥在雜志與日歷上的那些彩色風光照片,往往都將景色描寫得很溫和,給我們的感覺就像是我們可以安全地來來往往的一處游樂園一樣。而單色調照片具有一種很強烈的暗示,這個景色有另外一個層面,好似在這種場景里我們就像其他生物一樣,在自然的力量下是脆弱的,我們會輕易地就被水珠打濕的花瓣或是暴風吹動的云杉所觸動。雖然場景中并不存在危險的氣氛,但黑白影像卻會讓觀者感到或許有這種可能。
我喜歡這種霧氣氤氳,將背景成分都涂成白色的情調。尼康D2x 相機,12-24mm 鏡頭,ISO 100,f/16、1 秒 f/16
在大西洋的邊緣
我們以下面這個景象為例:想象一下我們現在正面對著大西洋,狂風中光線很快暗了下來;從務實角度很快就想到了黑白。海邊那大塊黑巖石曾經反射出來的色彩早就消失不見了。從這里到拉布拉多海岸之間沒有任何阻擋物,海浪一次一次地撞擊火山巖質的海岬,這正是絕佳的拍攝時機。拍黑白照是最自然的反應,而且它還能強調暴露感與脆弱感。
大多數彩色攝影師很喜歡在清晨和黃昏時分的濃烈的光線中拍攝,此時太陽剛好落到我們的額下,讓我們的畫面中洋溢著日或夜的可能性。這些照片含蓄地表達了短暫性,給觀者一種感覺,即使場景很有沖擊力,但它不久就會變暗,消失不見,或者變為陽光明媚,有益無害。但當我們用黑白來思考時,光線的色溫——不論基調是暖的還是冷的——都看不出來,因為沒有了光線所透露出的線索,所以可以很容易暗示不變和永恒。很難想象能比這種拍攝方式更好地表現場景的不變性了。黑白的表現力遠遠要超過一個陰霾天氣的效果。
天黑后不久,大西洋繼續書寫著它千年不變的故事。拍黑白,別無它選。尼康D3 相機,17-35mm 鏡頭,ISO 1000,f/13、1/2 秒
個人的印記
從安塞爾·亞當斯的時代以來,黑白攝影師就比那些彩色攝影師省去了很多表達上的多余成分。在亞當斯的一些作品中明顯地有一些奇怪的對比,與煙灰色的高堅濾光鏡相比,它并不能很好地表達事物的自然呈現,但煙灰色的高堅濾光鏡卻為人詬病。讓我們感到幸運的是,人們一般都會期待黑白攝影師不僅僅是一個記錄者;人們都會認為我們會將個人的印記留在場景中。人們通常的理解是,心思縝密的黑白攝影師絕不是不懂色彩語言的新手。如果一開始我們就清楚地了解何時需要用黑白來表現,別人就不會把我們當作兼職的彩色攝影師了。
我們通常總會把黑白照與風光攝影相聯系,但黑白照也可應用于野生動物的拍攝。
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用黑白來拍攝野生動物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在自然世界中,色彩是很重要的,無論是表現成熟的果實,表達“請勿靠近”的警示,暗示健康或是提供保護色。然而,一些攝影師開始認識到黑白的潛力,可以讓觀者重新審視他們認為自己已然熟悉的事物。
舉個例子,大西洋海鸚長著色彩鮮艷的鳥喙,所以很自然都會選擇用彩色照片來表現。那為什么要用黑白來拍攝呢?只是因為大多數人除了它花哨的喙和橙色的足,就沒有注意過這種鳥的整體形象。而且,黑白有效地強調了“他性”或者對象作為一種野生動物的事實,從而重新強調了我們的世界與鳥類的世界的不同之處。人類社會演變迅速,但動物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相對保持不變——黑白攝影揭示的是一種永恒性。
我在處理這張照片時力圖增強浴缸與周圍深暗的高沼地的對比。尼康D3 相機,17-35mm 鏡頭,ISO 640,f/18、1/40 秒
數據儲備
即便你的照相機有灰度模式或是黑白模式,也最好拍彩色,再在日后轉換成黑白,這樣你可以擁有更多的數據。
我要營造出一種高調的浪漫的氛圍,所以用了一只從Alien Skin 攝影器材專賣店購買的紅外濾光鏡。尼康D3 相機,500mm 鏡頭,ISO 800,f/5.6、1/1000 秒
黑白
當畫面中的形狀比色彩更重要時,可嘗試轉為拍黑白。
一定要了解的攝影史——走向社會風景
拍攝巖石的問題是,怎樣讓作品表現出更多的東西,而不僅僅是模糊的浪漫主義。這能夠做到,因為巖石跟街道一樣有意義,對我們來說都有重要意義——但是對于著眼于拍攝“現代”照片、能立竿見影的照片的攝影者來說,大都市里的素材既多又容易找到。從達蓋爾在圣殿大街拍攝第一張照片以后,街道便自然而然成為攝影者涉獵的場所,尤其是美國20世紀60和70年代的攝影者。
戰后對這種趨向有影響的攝影家,有沃克·埃文斯、維基和攝影聯盟的成員,紐約而不是巴黎成了他們主要的城市。紐約城展現出一片攝影視界,比起巴黎的人文主義街道更為清新。因此,盡管沒有明白加以界定,20世紀50年代的街道攝影,其實是“紐約學派”與“巴黎學派”的并立。如果說是對立,也許過于草率,但是不同的文化態度,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方法。
維基和他的《裸城》,以清新、積極甚至歡快的意圖,去面對生活中陰暗的一面。攝影聯盟及其社會紀實攝影計劃,使人產生了對紐約街道上每一方面的興趣。沃克·埃文斯帶來了概念化的拍攝方法,他的照相機就像是一個自動控制器。他在20世紀30和40年代后期,在紐約地鐵車站,把照相機藏在上衣底下,拍了一系列肖像照片。他對照相機看到些什么,只有模糊的概念,他唯一需要決定的事,就是在什么時候按下快門。他在芝加哥的街角,用同樣的辦法向攝影者證明,不看取景器同樣可以拍出滿意的照片。
由于以上種種影響,不知不覺便產生了一種風格。這種風格清新、即時、從容不迫、快速而有節奏感,色調猶如電影藝術。它的基調則是自然。有這種攝影風格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街頭攝影師,比如路易斯·福勒(Louis Faurer)和利昂·萊文斯坦。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帶來進一步影響的是兩個“外來者”——移居國外的威廉·克萊因和出生在瑞士的羅伯特·弗蘭克。克萊因的影響力主要在歐洲和日本,羅伯特·弗蘭克則對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攝影有很大的影響。他對美國尖刻的看法激怒了美國攝影界的保守人士,但對美國激進的年輕一代,卻起了點石成金的作用,年輕一代馬上迷上了嘲諷的、意識流的方法。他們中有加里·威諾格蘭德(Garry Winogrand)、李·弗里德蘭德、丹尼·萊昂(Danny Lyon)、布魯斯·戴維森(Bruce Davidson)和喬爾·邁耶羅維茨(Joel Meyerowitz)。他們視人文主義的方法為偽善,對此置之不理,而轉向尋常的題材,就像克萊因和弗蘭克那樣,用照相機來萃取自己生活經驗中的精華。
應該指出的是,他們的激進態度主要不在政治上,而在攝影上,雖然他們有點叛逆精神,并對政府有些不滿。他們的興趣更在于提取個人經驗,而不在于表現社會政治觀點。1966年,在藝術館館長兼導師內森·萊昂斯(Nathan Lyons)在羅切斯特的喬治·伊斯曼大廈舉辦的一次重要展出中,美國這一代攝影家中的佼佼者得以嶄露頭角。這次展出題名為“走向社會風景”(Towards a Social Landscape),描繪在弗蘭克觀點影響下的美國社會風景。可是,正像內森·萊昂斯在一篇目錄短論中指出的那樣,這些照片的個人意義絕不亞于其公眾意義。換句話說,這些照片固然是關于美國社會狀況的報道,但涉及更多的還是攝影者自己的感情。圖片中描述的社會風景是照相機和攝影師的腦海共同構筑而成,它既是真實的風景,也是如畫的風景。
“社會風景攝影家”的另一個主要支持者是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約翰·薩考夫斯基,這不是因為他想要站在他的前任愛德華·斯泰肯的對立面,而是因為他認識到社會風景是個新生事物。其目的似乎是跟斯泰肯倡導的新聞攝影正相反,從觀念上來說也確實如此,但是事實上,他們只是試圖要做嚴肅攝影者常做的事,就是用自己的語言合理地解釋世界。
1967年,薩考夫斯基在這十年間的另一次重要攝影展中,突出展出了威諾格蘭德、弗里德蘭德和戴安娜·阿巴斯的作品,把他們三人樹立為這一代攝影的領軍人物。薩考夫斯基在貼在墻上的題為“新紀實攝影”導言中,寫下了很有說服力的幾段話:
上一代大多數被稱為紀實攝影家的人,在紀實攝影還是一種新的提法的時候,把攝影作為對社會事業的一項服務。他們的目的是要說明世界上有哪些不對的地方,并試圖說服他們的同類行動起來去加以改正。
在過去十年中,新的一代把紀實攝影引向個人的目的。他們的目的不是去改造生活,而是認識生活。他們的作品顯示出對社會的脆弱與不完美的同情——幾乎是偏愛——的態度。他們喜歡真實世界,盡管這世界上存在著恐怖,但它卻是一切奇跡、魅力與價值的源泉,它的非理性并無損于其可貴之處。
他們都一致深信,平凡的事物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應該有勇氣去關注它,而少說那些空洞的大道理。
舉例來說,加里·威諾格蘭德是個悲觀、饒舌的人,他發現他能把他看到的,或者不如說是照相機取景框看到的生活圖景凝固起來。這聽上去很像卡蒂埃-布勒松,但事實上,威諾格蘭德的目的完全不同。
我拍照的目的是想看看,世界在照片上會是什么樣子。
就像當時很多的美國藝術,也像弗蘭克和克萊因一樣,對威諾格蘭德來說,拍照的行為比拍攝的內容更為重要。也許有人會說,“我拍照,所以我存在”。
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藝術博物館對攝影的興趣比以前增加了10倍,因此,威諾格蘭德這一代攝影師,甚至某些名義上的紀實攝影師,也在博物館的墻上為他們的作品找到了一個新的論壇。這促使他們更大膽地去拍攝完全個人化的作品,只考慮讓自己滿意,而不考慮讓任何其他人滿意,也許對博物館長是個例外。這是很有意義的一步,因為它讓威諾格蘭德和弗里德蘭德這樣的攝影家,得以擺脫商業任務的勞累。
也許有人會爭辯說,這樣的話,任何有意義的內容都舍棄了,剩下的只是照片框架里優美的形式,或者個人晦澀的沉思冥想。這便是對20世紀60和70年代街頭攝影師主要的批評所在,認為他們徒具形式,全無內容,他們對所拍攝的社會現實毫無興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像威諾格蘭德那樣的攝影家,他簡直像機關槍那樣去拍照——在他死后留下2500只沒有沖洗的膠卷,等于有90000張沒有讓人看到的照片——在他的照片里,也強烈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觀。我們可以把他刻畫成板起面孔的卡蒂埃-布勒松。威諾格蘭德拿起35毫米照相機來,肯定可以跟這位法國大師媲美,但威諾格蘭德是一個進取的,有時是嚴酷的攝影家,他的照片總是在憎惡人類的邊緣上搖擺,只是還沒有跨過這條邊線。他的街頭攝影師同行喬爾•邁耶羅維茨說他是“在大街上做心臟外科手術。他把皮膚割開,骨骼弄斷,好去接觸心臟,但一旦心臟暴露在外,他會極其克制地小心行事”。
任何公眾集會場所,都是威諾格蘭德的涉獵對象。雖然那暗示他所關心的只是事物的表面,但他的照相機卻像一把解剖刀那樣鋒利,他有著巴爾扎克那樣的分析頭腦。他創作的那些20世紀60和70年代的人間喜劇,是那個時期美國攝影最敏銳的記錄。
如果威諾格蘭德是巴爾扎克,那么弗里德蘭德便是那個冷靜而客觀的福樓拜;如果威諾格蘭德的興趣所在是人物,那么弗里德蘭德的興趣便是事物和場所。
弗里德蘭德是一個比他許多同代人和前輩都更冷靜的人。在氣質上,他更接近沃克·埃文斯,其次才是羅伯特·弗蘭克。在20世紀60年代,他開始以一種出色的新穎方式,重新涉足沃克·埃文斯的領域,即美國的小鎮風光。他在取景框里重新構建了風景,像個立體派畫家那樣把畫面折裂,再把美國市郊的高架線景觀和廣告牌景觀重新安排成形式復雜的照片,將平凡的事物描繪成一個全新的景象。與此同時,弗里德蘭德顯得稍稍有些不那么沉著,說明有什么地方不大對勁。他的作品不只是表述尋常事物,也涉及市郊生活中異化的一面。
弗里德蘭德是尤金·阿杰那樣百科全書式的攝影家。他曾游遍美國,到處去拍攝街景,也拍攝自然風光、樹木、花卉、爵士音樂師、他的家庭、裸體人像和他自己。看到過去45年中他拍攝的大量照片,人們一定會得出結論說,如果有一位攝影師,應該被認為是“日記式”攝影的激發者,這個人必定是李•弗里德蘭德。他的“作品”可以被描述為美國喬•埃弗萊奇(Joe Average)的“日記”——在提升了的層面上——是一切美國事物的詳細清單。他或多或少創立了一種意象,這種意象至今一直被美國攝影者進行著卓有成效的探索。
李·弗里德蘭德像威諾格蘭德,把弗蘭克的意象引進來,并使之本土化,別的攝影者也爭相效仿。到了20世紀70年代,一位名叫斯蒂芬·肖(Stephen Shore)的年輕美國攝影師花了六七年時間,進行了橫跨全國的旅行,拍攝了兩部重要作品——《美國外觀》(American Surfaces,1972-1973)和《不尋常的地方》(Uncommon Places,1973-1979)。前者是用35毫米照相機拍攝的,其內容不僅是肖所到之處,還包括他住宿的汽車旅館內部,甚至他的餐飲。他說:“我是在拍攝我的生活照。”所以在《美國外觀》中的照片,不只是快照模式,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快照。可是,當1973年他把他快照大小的照片在“光廊”展出時,它們的神態更接近于當時橫掃藝術界的一次新的運動——概念藝術。
肖接著繼續他的征途,這回他用的是大畫幅照相機,以沃克·埃文斯的精神來拍攝。《不尋常的地方》其實是一些再平常不過的地方,只是由于肖優美精確的視野才變得非同尋常。他曾拍過一張約塞米蒂谷的照片,那是安塞爾·亞當斯拍過好多他最出色照片的地方。但是肖拍攝的,不是巍然聳立的巖石,而是默塞德河畔的一群野營人。亞當斯把約塞米蒂谷拍成一片未受踐踏的荒野,而肖把它拍成一片市郊的游樂場。
現實的色彩
肖的“不尋常的地方”,標志著美國風景照的一次轉變,從根本意義上說,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拓性和獨創性。它是彩色的。從前,大多數“嚴肅”的攝影者把彩色看成是“庸俗”,是廣告,是時尚和旅行攝影師的本職。羅伯特·弗蘭克曾經說過,“黑與白乃是攝影的色彩”,很多攝影者都同意他的說法。不過這種態度正在漸漸改變,一是因為攝影器材一年年在改進,二是因為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問題。攝影者開始意識到黑與白并不是自然的顏色,它給現實與影像之間造成了很大的隔閡。再說,有些攝影者認為,黑與白會使看到影像的人立即產生懷舊感。“所有的照片都是歷史”固然不錯,但他們想要表現的是此刻,是現在,他們認為色彩更適合這項任務。
在20世紀70年代初,還有不少人對彩色持反對態度。可是等到一位彩色攝影者得到約翰•薩考夫斯基和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認可之后,便大局已定了。1976年,薩考夫斯基展出了孟菲斯市一位名不見經傳,叫威廉•埃格爾斯頓(William Eggleston)的攝影者的作品。不少人對此感到迷惑——埃格爾斯頓似乎把“美學快照”發揮到了極致。他顯然隨手拍攝了一些照片,諸如一條狗在泥潭里喝水、扔在床底下的鞋子、一輛兒童三輪車,以及一些雜亂的、空無一物的風景照等。約翰·薩考夫斯基把埃格爾斯頓的風格描述為“完美無缺”。《紐約時報》的藝術評論員希爾頓·克雷默(Hilton Kramer)的看法則完全不同。
完美?也許是陳腐而平庸的完美,但肯定是枯燥無味的完美。
但不管怎么說,威廉·埃格爾斯頓隨同展覽發表的《向導》(Guide)一書,卻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著作,書中的有些照片,是近代攝影作品中最為人稱道的。
威廉·埃格爾斯頓的《向導》中所有的照片,都拍攝于南方內地。他的主要題材,以及照片中的含義,都是關于私人的。有一點可以肯定,他運用色彩和一切手法從形式和心理上來表現形象,但不讓這些壓倒內容。這些形象,一般不會用黑白來表現。就像當時許多美國攝影者的作品一樣——無論是黑白還是彩色的——它們表現的是平凡事物的美學潛質。色彩是外加的元素,它賦予另一層次的意義。這層意義,許多攝影者現在往往試圖在作品內部將它顯示出來。
紐約,希爾克雷斯街,1970年 明膠銀印
李·弗里德蘭德拍下了我們平時不大注意的電線桿、電線、招牌,以及那些把城市環境弄得亂七八糟的馬路雜物,創造了表現平凡事物的新攝影。他通過不時把自己置身于相框之內,宣稱當代攝影既是視覺紀實,又是個人表現的媒介。
在20世紀60年代,李·弗里德蘭德以拍攝美國市區的照片而名聞遐邇。他以閑適深情的目光,看著美國市鎮的日常街景。他跟威諾格蘭德和其他同代人一樣,是為了個人原因,而不是為了社會來拍攝紀實照片的。從表面上看,他的出發點是在形式方面。弗里德蘭德用大街上的事物來打破畫面的空間,創造出奇特的比例,以及我們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視覺的混亂妨礙了形象最初的親切感,并被描述為對我們今天的隔閡感是一種有效的隱喻。
弗里德蘭德的街景,以及偏斜的自拍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用電線桿把相框分隔開來現在成了老一套的構圖手法,可是弗里德蘭德的早期照片,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這種手法。這些照片,至今仍光彩熠熠,其視覺上的才智和構圖的奇特意味深長。瑪莎·羅斯勒(Martha Rosler)寫道:“這些照片,從攝影上的逗趣到玄學上的沮喪,幾乎無所不包。”
羅斯勒還把弗里德蘭德刻畫成“在一個瘋狂的、機械般的世界上的孤獨的人”。不過那也可能用來解釋他的照片的迷人之處。城市景觀和俏皮的自拍像,從視覺和感情上記錄了我們在現代城市中的經驗。
美國軍團集會,得克薩斯州達拉斯,1964年 明膠銀印
雖然加里·威諾格蘭德跟卡蒂埃-布勒松一樣,是35毫米照相機攝影大師,但是他的世界觀卻很難說是積極的或者人本主義的。他曾經寫道:“我們不愛生活”。這句話充分反映了他視野的悲觀性質。
這張照片是典型的對相框內形式的完美安排——盡管既不經典,也不明顯——我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會被那殘疾人所吸引。他顯然流落在一個無視于他的不幸的、不關心他人疾苦的世界。似乎威諾格蘭德也是個無視他人的苦難,甚至沒有憐憫之心的攝影師。他的脾性是屬于那種憤憤不平,甚至憤世嫉俗的類型,但人們并不認為他是那無目的的一代中最主要的攝影師,他的作品,比起乍看似乎是嘲諷的表面更要復雜得多。他對大街上的一切東西都很感興趣。可是,雖然他傾向于把他看到的一切轉化為他個人的抒發,我們看到的依然是紀實照片,是美國近代歷史中最困擾、最有魅力時期的輝煌紀實。
據說威諾格蘭德就像馬丁·帕爾一樣,對他拍攝的人物并不怎么關心,經常對他們加以嘲諷。不錯,他的影像尖銳到了辛辣的程度,可是他跟帕爾一樣,既溫柔又殘酷,悲觀主義通常占了上風。事實上,他那一大批散亂的作品,時而熱情奔放,時而悶悶不樂。要說到他的最高成就,那該說他是我們見到過的最杰出的街頭攝影師。
大賽馬日 明膠銀印
當托尼•雷-瓊斯在美國學習攝影后,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回到英國的時候,他認為英國是一片攝影的沙漠。他仿佛是第一次看到故土,這促使他以一種對英國攝影產生深遠影響的方法來拍攝英國的紀實照片。
托尼·雷-瓊斯(Tony Ray-Jones)的攝影取材于英國海濱及那里的習俗,這是因為英國人只有在海濱和聚會中,才會拋下固有的保守,充分展示他們的天性。雷-瓊斯在這方面的探索中,不僅帶些幽默,還略微顯示出從瓊·維戈(Jean Vigo)的電影以及比爾·布蘭特的攝影中學來的超現實主義色彩。同時,他還著意于從加里·威諾格蘭德和羅伯特·弗蘭克等街頭攝影家那里學到形式上的技巧。雷-瓊斯把美國攝影風格大師主觀紀實的拍攝方法融入他的新題材之中,和大衛·赫恩(David Hurn)、伊恩·貝里(Ian Berry)和約翰·本頓·哈里斯(John Benton Harris)等人一道,給英國攝影注入了新的氣息。
其結果正如這張賽馬日照片所顯示的,是一幅形式上復雜的影像,從中可以看出英國人之所以成為英國人的一種癖好。一匹馬走進一間電話亭,一位男士在全神貫注地吃冰激凌。當然,這是虛構的。雷-瓊斯用老一套手法,合成了一幅英國圖景。他讓英國人看到一幅描繪自己的圖畫,可以叫他們發笑,也可以讓他們欣賞。它缺少政治意味,但包含著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螃蟹,斯金寧格羅夫,1981年 明膠銀印
如果說托尼·雷-瓊斯關于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紀實攝影缺少政治焦點,那么對于80年代的英國社會風景攝影家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和克里斯·基利普(Chris Killip)來說,情況絕非如此。基利普拍攝的撒切爾時代蕭條的東北部滿是沙礫的海灘,所描繪的情景和雷-瓊斯拍攝的舒適的海濱休養地迥然不同。
基利普拍攝的是北約克郡斯金寧格羅夫東北部的鄉村,以及諾森伯蘭郡的萊恩茅斯。他在萊恩茅斯拍攝了約40張流動露營者的生活照片。這些人靠撿拾被海水沖刷到海灘上的煤塊為生,而那些煤塊,原是煤礦作為廢渣傾倒掉的。如果說托尼·雷-瓊斯關于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紀實攝影缺少政治焦點,那么對于80年代的英國社會風景攝影家約翰·戴維斯和克里斯•基利普來說,是花了很多工夫去熟悉拍攝對象,因此,他們的照片可以說是深諳內情的人的作品。
斯金寧格羅夫是蒂斯都市圈和風景如畫的惠特比漁港之間的一個小小漁村。住在附近的人說,“斯金寧格羅夫是把自己的嬰兒吃掉的地方”。這句話表明那地方的某些特點——貧困、心懷不甘的工人階級,以及對高雅的抗拒,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是如此。
這張照片并不輕易泄露它的秘密。它幾乎明白無誤地闡明,為什么“紀實”和“詩意”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字眼,會經常被運用在一起。這是一張“等待”的照片,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輛嬰兒車和兩條狗,都處在有目的的警覺狀態之中。尤其是那名男子,在堅定地凝視著大海。他們在等待什么?一條返港的船嗎?女人身旁的一箱螃蟹說明,至少有一條船已經把捕獲物卸到岸上了。可是在一座小漁村里,直到最后一條船都平安返港之前,岸上的人只能焦急地注視著,等待著。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