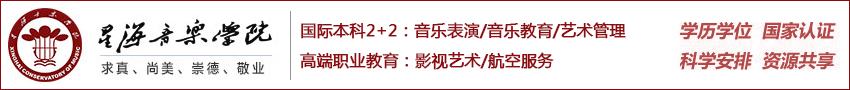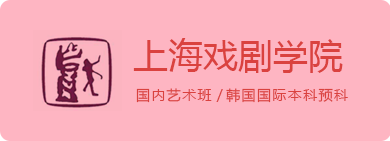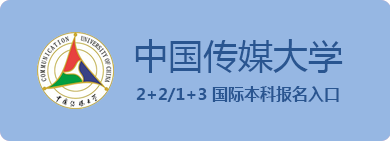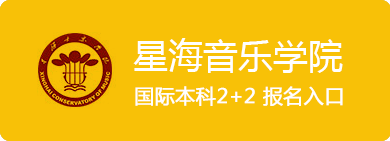播音主持自備稿件:《啞娘》
我出生時,由于父母鬧離婚,我被送到了鄉下,讓一個長得像男人一樣五大三粗的啞巴女人當我的媽媽,她就是我的啞娘。
在我去啞娘家之前,啞娘出生三個月的孩子夭折了,于是,我成了啞娘和她的丈夫駝背叔的精神寄托。他們把我當成親生兒子,把所有的關愛都給了我。駝背叔會吹嗩吶。那時,每逢村里有紅白喜事,駝背叔都會被請過去。只要駝背叔的嗩吶一響,周圍的喧囂立刻停止了。男人們忘記了抽旱煙,女人們忘記了納鞋底,孩子們不哭不鬧了,紛紛睜大了好奇的眼睛。駝背叔的手指輕輕抖動著,或悠揚,或哀婉,或激昂的曲子便從手指間汩汩流淌出來。《百鳳朝陽》鳥語花香,《風攪雪》氣勢磅礴,《十面埋伏》扣人心弦,《哭墓》讓人斷腸……
每次吹完,紅白喜事的主人除了給駝背叔一點錢外,還會送上在當時極為珍貴的肉夾饃——雪白的饅頭,油汪汪的肉,看了就讓人流口水。駝背叔舍不得吃,把肉夾饃揣在懷里,還給我。看著我香甜地吃完,駝背叔和啞娘總會笑得很開心。
大雪紛飛的日子里,啞娘把土炕燒得暖暖的,我依偎在啞娘的懷里,邊看著啞娘納鞋底,邊聽著駝背叔吹嗩吶。駝背叔的嗩吶總能把我的心帶向很遠很遠的地方……
然而,好日子總是短暫的。
在我四歲那年,駝背叔忽然得了一種怪病,死了。我清晰地記得,駝背叔臨終前,眼解掛著一滴淚。那滴淚在秋陽下抖動著,閃爍著,年幼的我示能從那滴淚里讀出什么,直到現在才明白,那滴淚里滿含了牽掛和不舍。
駝背叔走后,村里人都勸啞娘把我送回去,趁年輕改嫁個好人家。啞娘緊緊地抱著我,拼命地搖頭,時不時地用滿是驚恐的眼睛向四周望一望,仿佛怕別人把我從她的懷里搶走。
沒有駝背叔的日子里,我和啞娘相依為命,日子過得很艱難。啞娘惟一能掙錢的活計是做豆花。每天深夜,在昏暗的燈光下,啞娘推著沉重的石磨,一圈圈地轉著,看著潔白的豆漿汩汩流出,磨完后,啞娘不顧得抹去沁滿額頭的汗珠,又把豆漿裝入大瓦缸,端上鍋,生起火,這時,她才能稍稍喘口氣。
天不亮,啞娘便領著我出門了。啞娘不能叫賣,只好拿起駝背叔留下的那把嗩吶,用嗩吶代嘴叫賣。由于底氣不足,啞娘總把嗩吶吹得很刺耳,那刺耳的嗩吶聲伴隨了我整個童年。沉睡中的人們聽到嗩吶聲,就披著衣服,惺忪著朦朧睡眼,把一張張毛票遞給啞娘,換取一碗碗熱氣騰騰的豆花。
村里的孩子看見啞娘,總跟在她后面起勁地喊:“啞巴婆,吹嗩吶,嘴巴鼓得像蛤蟆……”啞娘沒有聽力,聽不到他們在說什么,不時地回過頭沖他們笑一笑。
我漸漸懂事后,啞娘成了我的恥辱。每次和同學們在一起玩時,總有人用手做出吹嗩吶的樣子,發出怪叫。這時,其他人就哄堂大笑。我拼命捏緊了拳頭,臉漲得通紅,不知該轉向哪里。
我回到家,大聲向她喊:“你為什么是個啞巴?為什么!你送我回我自己的家,我再也不要呆在這兒了!”
啞娘聽不見我在說什么,但她似乎從我的表情中讀出了什么,默默地站在一邊。淚,像從傷口流出的鮮血,無聲地順著啞娘的臉頰靜靜地流淌著……
以后的日子里,我很少搭理啞娘。我把同學們對我的嘲弄全化成了對啞娘的仇恨。那時,我只有一個愿望:趕快考上初中,去縣城讀書。那樣,就不會有人知道,我有一個啞娘了。
終于,小學畢業了,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縣一中。我住進了學校,一個多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啞娘都會打量我許久。當她伸出手,想摸摸我的頭時,我會把冰冷的目光投向她。啞娘伸出的手就怯怯地縮回了,她的臉上有孩子般的不知所措和難過。
初二那年冬天,我感冒了,周末沒有回家。星期天早上,我正在宿舍里躺著,忽然聽到了熟悉的嗩吶聲。是啞娘的嗩吶聲!我的心急速地跳了起來,難道是啞娘來了嗎?
許久,我走出宿舍。屋外,飄著大朵大朵冰冷的雪花……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