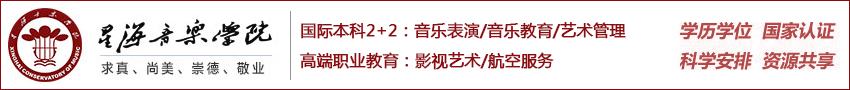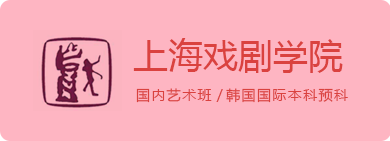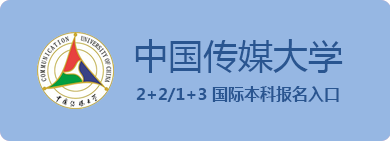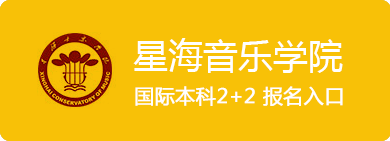播音主持自備稿件:《秀色》
男:沿太行山西路一直向上,有一個名叫秀色的村子。秀色山高路陡,樹木也欠繁茂,只有幾十戶人家,可秀色有名。
女:秀色的有名,不在于它的山高路陡,不在于它的村民稀少,也不在于它這別致的稱謂,秀色的出名,在于它缺水。
男:吃水,要走一百里的山路下山去背,背回來的水是要上鎖的。在秀色,值得上鎖的東西只有水。三幾寸長的鐵鑰匙,掛在一家之主的腰間,顯示著主人的尊嚴,也顯示著水在秀色的神圣不可侵犯。
女:方圓百里的村寨,那些當娘的,嚇唬閨女時就說,小丫頭再不聽話,長大把你嫁到秀色去。
男:眾人哄笑起來。秀色的村長張寶便說,論風水呀,別處還比不了我們秀色。
女:風水風水,得有風有水。你秀色呀,還缺著風水里的一大項呢。
男:除了沒水,我們什么沒有啊?
女:喲,這連 水都沒有,它還能有什么呀?
男:一句話,噎得張寶羞愧難當,連水都沒有,還能有什么呢?那么該找水脈吧,該打井吧,該上縣里、上省里請打井隊吧。從前那些年,這些事都辦過。本縣的打井隊一聽秀色就犯怵,來都不肯來;外縣的打井隊好不容易請來了,但只二十天,他們便熬不住了。村里人使盡了各種辦法,還是沒能留住他們。
女:十多年過去了,秀色依然沒有水,而那句“連水都沒有,還能有什么”的咒語,依然壓在秀色人的心頭。
男:村長張寶又去了縣水利局,新來的局長人稱李技術的,專注的聽了他的講述,決定親自去那里看看。經過半個多月的實地勘察,他料定秀色有出水的希望。于是帶齊人馬,上秀色打井。
女:二十多天過去了,井是越打越深,人是越來越瘦啊,可還是不見有水。村里的氣氛,漸漸慌亂了起來,莫非,這莫非是又到了從前經歷的那關口?再不見水,這群人又該走了呀。
男:打井隊的人都住在村民們家里,李技術住在張寶家。張寶家有個十七八歲的大閨女叫張品,是秀色姑娘里出眾的人物。她知道,再不見水,她的青春就滅了。她知道青春是什么,更知道青春在秀色的位置是次于水的。
女:這天晚上,張品望著正屋里上了鎖的水廚,對娘說,叫我砸了它吧。娘問她干嘛。張品低了頭說,洗洗。娘明白了,卻不上手。張品親自砸了鐵鎖,將水揮霍一空。
男:李技術從井上回來,進了屋,一下子見到張品,忙背過臉去說,你,你的衣裳呢?快穿起衣裳。
女:今天晚上,我沒有衣裳。
男:別胡來啊,沒有衣裳也要穿起衣裳。
女:胡來?我這是胡來?
男:不是胡來你為什么這樣?
女:為給你看看。我使盡全家半個月的水,就為這,你還敢說胡來?
男:快走,快走。好,你不走,你不走我走。
女:你往哪去?
男:往山下走,下山,回家。
女:回家?這才是你的心里話吧,我早就看出來了。白搭,就是把全村人的心都挖出來,也換不來你們給打一口井。白搭呀,該給的都給了,沒給的,就剩我們這些閨女了呀。
男:你不能這樣,你不能。
女:張品一下子撲進李技術懷里,雙手緊緊箍住他的腰。
男:放手啊你。你怎么這樣,這樣沒有廉恥。
女:在沒有水的地方,你還指望誰有廉恥?
男:這一夜,他們不再有話,就這樣僵持著。天亮了,李技術揉揉通紅的眼往外走。
女:你去哪?
男:打井。
女:第二天,李技術從張寶家搬了出去。打井隊在井邊搭了帳篷,吃住都在帳篷里。他們瘋了似的打井,頭發不剃、胡子不刮,身上酸臭撲鼻,山鬼似的。
男:沖擊鉆,狠狠的刺向井深處。每刺一下,李技術在心里說,這一下,是為張品;這一下,是為張品;這一下,是為張品的;這一下,還是為張品的。
女:九九八十一天,打井隊沒人下山回家。九九八十一天吶,九九八十一天,他們終于把井打出了水。
男:村民們先是對這井中的泉水又驚又怕,生怕這不過是土炕上的一場大夢。
女:然后,然后他們才放開肚量暢飲,他們讓這久違了的干涼的水給醉得東倒西歪呀。
男:那是個初夏的艷陽天,那時秀色人最得意忘形的日子。
女:這時候,李技術弄明白了一件事。在那個羞恥的晚上,羞恥的本不是張品,羞恥的該是他本人吶。
男:共產黨的打井隊,若是給老百姓打不成井,那么最后渴死的不是自己,又是誰呢?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
掃碼關注,實時發布,藝考路上與您一起同行